【案情简介】
韩某于1983年入职深圳海关并担任关务员,负责货车载货及旅客行李检查等工作,1990年离职后以经商为业。2016年7月5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由,将韩某刑事拘留。检方指控:2014年3月至5月间,韩某以找海关人员疏通关系、帮助于某获得从轻处理为由,多次通过他人向于某的家属孟某索取钱款共计35万元。韩某利用其原在深圳海关任职形成的便利条件,找到深圳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孙某、梁某,企图在于某案件退回深圳海关缉私局补充侦查后,让上述工作人员能利用职务之便给予相应帮助,但于某所涉刑事案件没有明显进展。
2017年2月27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韩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韩某虽然表示认罪,但其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希望二审可以获得轻判,因此提出上诉。该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韩某花费了10万元聘请律师,但效果并不理想,律师所提出的关于韩某属于犯罪未遂、自首的罪轻观点均未被一审法官所采纳。上诉后,韩某并未继续聘请律师为其辩护,未曾想到二审法院深圳市中院的法官主动联系韩某,询问他是否需要法律援助,在得到韩某肯定的答复后,2018年1月10日,深圳市中院通知深圳市法律援助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以及有关规定,请深圳市法律援助处为韩某指派辩护律师。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根据该“办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以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收到深圳市中院关于为韩某指定辩护律师的通知时,恰逢黄云律师参加深圳市司法局的调研会议,会后深圳市法律援助处领导询问黄云律师是否有意承办这个案件,黄云律师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法援处的安排,担任韩某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指派后,黄云律师立刻前往深圳市中院调取案卷,研读本案所有卷宗材料,对侦查机关对本案追诉活动的全部过程进行合法性审查,剖析一审阶段公诉方据以证明指控主张的证据体系,发现这一证据体系的漏洞和缺陷,理顺一审法院认定韩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逻辑,并多次与韩某沟通,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黄云律师率领团队成员对案件进行了多次研讨、论证,最终在对本案深入的分析后,决定为韩某制定无罪辩护策略。结合全案证据材料,依据事实、证据、法律提出了“精准、有效”的辩护意见。
黄云律师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制定辩护策略:1.何谓“影响力”?2.韩某对涉案海关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影响力?3.即使认定上诉人韩某对涉案海关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影响力,其在本案中没有也不可能利用该影响力。
黄云律师向法庭递交二审开庭审理申请书,2018年5月29日,法庭开庭审理此案件。在庭审中,黄云律师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关于刑法意义的“影响力”含义问题。
在刑法语境中,“影响力”应理解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够影响和改变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和行为,让其在行使职权时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回到本案,如果要认定上诉人韩某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首先必须证明上诉人对深圳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影响力,其次必须证实该影响力改变或影响了深圳海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和行为,并致使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是否存在徇私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事实。
黄云律师认为,上诉人韩某对梁某、孙某均不具有“影响力”,其行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韩某对涉案海关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影响力
首先,上诉人韩某于1983年至1990年期间先后在沙湾海关、文锦渡海关、罗湖海关工作,系海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但事实上,并非只要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就一定具有影响力。案卷证据表明:第一,上诉人韩某对于帮助于某一事是否可行无任何把握;第二,上诉人韩某并不知该事情该如何操作。这也就说明韩某并不知其在该事情上是否有影响力,更不知道影响力的支点何在?
其次,上诉人韩某与孙某虽在三十年前曾为同事,但是否可以简单的据此得出上诉人韩某对孙某具有影响力呢?
现有证据仅能证实上诉人韩某与孙某曾有一段短暂的同事关系这一基础事实,但却无法直接得出他们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结论。根据孙某的陈述,其与上诉人韩某仅共事一年,其后在韩某离职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其与上诉人韩某几无交往,作为一般社会人根本无法仅以此得出上诉人韩某与孙某关系密切的结论,更无法据此得出上诉人韩某对孙某具有影响力的结论。
3、即使认定上诉人韩某对孙某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影响力,其在本案中没有也不可能利用该影响力
假定法庭简单地以上诉人韩某曾在三十年前与孙某系同事为由,而认定上诉人韩某对孙某具有影响力,进而认定其构成利用影响力犯罪,则必须得证明上诉人韩某“利用”了该影响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见,不管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还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该主体所具有的影响力所影响对象均为“国家工作人员”。
假定基于上诉人韩某与孙某三十年前的同事关系而认定对其具有影响力,因孙某在2014年3月份已离职,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上诉人韩某想通过其并不存在的影响力影响孙某也已无可能,属于刑法上的“不能犯”,故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诉人韩某利用了其 “本不存在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黄云律师认为,韩某涉案收取35万元的行为不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二审法院深圳市中院认为,本案中,附案证据所证实的案情事实,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韩某所实施的相关行为唯一地只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相关联。因此,其行为并不确定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构成的要求,故原审判决有关“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依据不具充分的排他性、认定依据不足。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撤回一审判决,上诉人韩某无罪。判决书全文也紧紧围绕着黄云律师的辩护意见进行说理论证。
法院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影响力”,其能力的来源只限于职权、(与工作、职务相关联而形成的)地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尽管那些因(原)职权、地位或公务关系所形成的情感、亲缘等关系,其自身客观上可能足以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影响力,但这些影响力并不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所规定犯罪行为中的影响力的形成因素。因此,已离职的行为人能够利用、且是基于过往的职权或地位而形成的影响力,因随时空变迁,影响能力本身是否会存在消减的可能,并且导致能力对外作用效能亦随之变化?应当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严格限定已离职人员影响力的散发边际,已离职人员的离职时间长短,在职时的任职情况等问题均应当成为重点评价的事项。因为能够维系人与人交往关系的,除了权利、地位或工作联系因素外,毕竟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素,且这些因素还未见得一定要与权利、地位或工作联系等因素交汇后才能对维系人与人的交往起到作用。
综上所述,本案附案证据所证实的案情事实,尚不足以证明韩某的行为唯一地只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相关联。原因有三:第一,法条中有关“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系属客观要件范畴,并不宜将其归入主观要件之中。本案,原审所作“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证据支持。第二,如果当事人因曾经的工作联系得以结识一众同事、朋友,并于其离职后继续维系双方联系的行为只能被理解为具有“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属性,并据此对相关当事人定罪归责,那么,刑法的运用是否会有欠谦抑,是否会过于恣意。第三,从职位上看,韩某担任公职期间只是最基层的关员,其只有被领导的可能,因而其与其他海关工作人员形成的只是一般的同事关系。并且,本案发生距韩某离职相隔24年,作为具有公职身份时也只是一般公职人员的韩某,其几无可能再基于原职权或地位而对其他公职人员产生影响,韩某所找寻的原海关同事孙某即使愿意提供帮助,基于的也完全可能(亦即不能排除)是由原同事关系发展而来的朋友情谊或原同事的情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上诉人韩某无罪。目前,检察院未提出抗诉。
【案件点评】
本案,黄云律师以韩某二审指定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本案,秉承专业精神,细细研读卷宗材料,广泛检索法院相关判例、专家学者观点。对于案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周密论证,以“影响力”作为辩护的核心,对韩某的涉案行为逐一进行了分析,从而促使本案的二审法院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充分解读,结合本案被告人韩某在海关工作期间所担任的具体职务,明确了韩某的行为性质,最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无罪判决结果。
本案的宣判,对于正确理解刑法的运用有重要意义,“罪刑法定”是刑事法治领域的重要根基,刑法并非囊括所有不合理行为的“口袋”。刑法在立法之初及运用之时均应保持谦抑,如果该案中韩某最终被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量刑,那么日后那些与某一罪名模糊相似、有关或者不好定性行为,是否都将被仓促地按照类似的罪名处理?如此一来,这些罪名又与“口袋罪”有何异?预先为行为人设定罪名并对其行为进行反推是危险的,可能导致刑事司法中的实质类推的存在,亦增加了刑法重刑主义、刑法工具主义的色彩。
韩某该案虽是个例,但更多的类似案例依然存在,当某一行为所涉罪名之罪过形式规定或其罪状描述不明确等足以影响行为人定罪量刑的情形发生时,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辨别行为的具体性质,明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界限,不应对刑法条文随意理解逾越扩张解释的界限,或是根据喜好有选择性地执法而随意出入罪。树立严谨的法律精神和文化,优化法律的解释和运用,惟此最终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司法公正。
附件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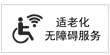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2963号
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2963号